男女主角分别是陈渊李富贵的其他类型小说《穿越明朝:无敌学霸的打脸日常 番外》,由网络作家“字渡人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陈渊只觉太阳穴突突直跳,视网膜上残留的现代图书馆白炽灯光斑尚未消散,鼻腔却先被一股陈年老木与霉味混合的浊气撞得生疼。他踉跄着扶住桌角,指腹触到斑驳的木纹——那是张虫蛀严重的槐木书桌,桌面凹痕里积着半寸厚的墨灰。抬眼望去,四面土墙上贴满泛黄的八股文习作,窗棂漏进的细尘在斜光里浮沉,像极了他前世在博物馆见过的明代私塾复原场景。“这是......”喉间泛起铁锈味,他惊觉自己竟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襕衫,袖口磨出的毛边刺着腕骨。原主记忆如碎玻璃般刺入脑海:陈渊,凤阳府怀远县人,县试第一的寒门秀才,三日前背着半袋粟米徒步百里赴应天府乡试,借住在城西破落学舍,因交不起文会贽见礼,被本地士子视为笑柄。“咚”地一声巨响,雕花木门被踹开。六个锦衣少年鱼贯...
《穿越明朝:无敌学霸的打脸日常 番外》精彩片段
陈渊只觉太阳穴突突直跳,视网膜上残留的现代图书馆白炽灯光斑尚未消散,鼻腔却先被一股陈年老木与霉味混合的浊气撞得生疼。
他踉跄着扶住桌角,指腹触到斑驳的木纹——那是张虫蛀严重的槐木书桌,桌面凹痕里积着半寸厚的墨灰。
抬眼望去,四面土墙上贴满泛黄的八股文习作,窗棂漏进的细尘在斜光里浮沉,像极了他前世在博物馆见过的明代私塾复原场景。
“这是......”喉间泛起铁锈味,他惊觉自己竟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襕衫,袖口磨出的毛边刺着腕骨。
原主记忆如碎玻璃般刺入脑海:陈渊,凤阳府怀远县人,县试第一的寒门秀才,三日前背着半袋粟米徒步百里赴应天府乡试,借住在城西破落学舍,因交不起文会贽见礼,被本地士子视为笑柄。
“咚”地一声巨响,雕花木门被踹开。
六个锦衣少年鱼贯而入,最前头的胖公子摇着撒金折扇,腰间羊脂玉佩撞在门框上,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
陈渊认出这是南京通判之子李富贵,昨日在贡院外见过,此人左眼角有颗朱砂痣,此刻正随着他的冷笑微微颤动。
“哟,这不是画地图的穷酸鬼吗?”
李富贵拖长音调,折扇“啪”地展开,扇面上“富贵闲人”四个金粉大字晃得人眼花。
他逼近两步,陈渊嗅到对方身上浓郁的沉水香,与学舍里的霉味混在一起,令人作呕。
“听说你昨晚在墙上画了个什么劳什子舆图?
怎么,想靠泥巴点子巴结考官?”
哄笑声中,一个瘦脸书生挤到前排,指尖戳向陈渊肩头:“我等在聚贤楼吟诗作赋时,你怕是在啃窝头吧?
瞧瞧这衣裳——”他突然伸手一扯,陈渊右袖“刺啦”裂开道大口子,露出瘦骨嶙峋的小臂。
“这补丁针脚,比我家狗啃的还乱!”
周围爆发出更大的笑声。
陈渊攥紧拳头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他看见李富贵身后站着个灰衣老者,腰间挂着贡院腰牌,正是昨日监考的吏员。
原主记忆里,此人总在考场后巷与考生私语,此刻正用眼角余光瞥向自己,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。
“诸位说完了?”
陈渊听见自己的声音竟意外平稳。
他转身走向书桌,从笔筒里抽出半截炭笔——笔尖早已被磨得秃钝,却
在触到墙面时突然变得流畅。
前世研究明史时烂熟于心的《皇舆全览图》细节如潮水般涌来,他手腕翻飞,岷山、长江、钱塘江口依次在灰墙上浮现,甚至连崇明岛新生沙洲的轮廓都分毫不差。
“这......这是《大明田亩舆图》?”
有人倒吸冷气。
陈渊眼角余光看见李富贵的脸色由红转白,折扇握柄处青筋暴起。
他故意加重笔触勾勒出凤阳府地界,指尖在“怀远县”三字上顿了顿——那里有原主记忆中坍塌的土坯房,和母亲临终前塞给他的半块饼。
夜更深了。
陈渊摸着黑走向茅厕,木屐踩过积水的石板路,发出“嗒嗒”声响。
路过东厢房时,门缝里漏出的烛光突然晃了晃,他本能地贴紧墙根。
“......《春秋·僖公篇》第三题,切记切记。”
是李富贵的声音,带着几分不耐。
“放心,这次卷子由我亲自批,只要你......”另一个声音低得像蚊子,却让陈渊瞳孔骤缩——那是今日在场的灰衣吏员。
他屏住呼吸,悄悄凑近门缝。
透过竹帘缝隙,看见李富贵正将一锭白银推过桌面,吏员伸手去接时,袖口滑落,露出小臂上的朱砂痣——与李富贵眼角那颗竟一模一样。
陈渊心中剧震:原主曾听人说过,这吏员是李府远亲,却不想竟明目张胆到在学舍内交易。
“三日后府试,若出了差错......”李富贵突然提高声音,陈渊急忙后退半步,鞋底碾到一片枯叶,发出细碎的“咔嚓”声。
屋内骤然 silence,他转身就跑,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拐过墙角时,他瞥见月光下自己的影子——青衫破洞在夜风里翻飞,像一面破旧却坚韧的旗帜。
回到房间,陈渊摸出藏在墙缝里的炭笔,在掌心写下“僖公篇”三字。
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梆子声,梆声三下,惊起檐下宿鸟。
他摸了摸裂开的衣袖,忽然想起前世导师说过的话:“历史从不给弱者怜悯,却会给清醒者机会。”
指尖轻轻抚过墙上未干的舆图,在应天府位置画了个圈——这里,即将成为他的战场。
远处传来五更天的鸡鸣。
陈渊吹灭油灯,黑暗中,墙上的线条却愈发清晰。
他躺下时,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,混着远处护城
河的水声,织成一张细密的网。
这一夜,他没有合眼,脑海中反复推演着府试的每一个细节,直到窗纸泛起鱼肚白,才终于露出一丝冷笑——李富贵,就让你看看,什么叫做真正的“金手指”。
府试那日,陈渊特意换上补丁最显眼的襕衫,腰系碎玉,混在锦衣考生中格外扎眼。
贡院高墙外的槐树叶簌簌落下,他踩过满地碎金,在考棚前接过题纸时,故意让指尖抖了抖——监考官王大人抬眼瞥他,目光在破袖口上停留片刻,嘴角掠过一丝嫌恶。
考题果然是《春秋·僖公篇》。
陈渊摊开宣纸,墨块在砚台里磨出细腻的浆,却在写下“春王正月”时故意顿笔,将“正”字竖画拖得老长,形如蚯蚓。
第三行《悯农》诗抄到“四海无闲田”时,竟错写成“四海无良田”,笔下歪斜不堪,活像学童涂鸦。
“可惜了这县试第一。”
隔壁考棚传来窃笑。
陈渊不用抬头也知道,是李富贵的跟班张公子。
那人昨日在学舍见过墙上舆图,此刻定以为自己胸无点墨,全靠运气进的考场。
日头偏西时,陈渊搁下狼毫,活动发麻的手腕。
最后一页纸上,“税改七策”四个大字力透纸背,他蘸饱墨,写下第一句:“夫民者,国之基也,基固则国宁,基摇则国危。”
笔锋陡然一转,从明初鱼鳞图册讲到土地兼并之弊,再到“一条鞭法”的雏形构想,字字如刀,直剖时弊。
王大人收卷时,目光扫过陈渊的试卷,先是眉头紧皱,待看到后半部分,瞳孔突然缩紧,手指捏着纸页发出“簌簌”轻响。
陈渊起身时,故意让袖口拂过砚台,墨汁溅在王大人官服下摆,他慌忙赔罪,却在弯腰时瞥见对方腰间玉佩——正是昨夜在李富贵厢房见过的款式。
三日后放榜。
应天府衙前人声鼎沸,陈渊站在榜下,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惊叹声。
李富贵的名字歪歪扭扭挂在末位,而他的名字,端端正正列在榜首。
“不可能!”
杀猪般的嚎叫从身后传来。
李富贵挤开人群,胖脸涨得发紫,手指戳着榜单上的“陈渊”二字,指甲几乎抠破黄纸,“他昨日卷子错漏百出,定是买通了考官!”
人群顿时哗然。
陈渊转身时,正看见王大人从衙内走出,额角沁着细
汗。
他向前半步,作揖道:“李公子既说陈某舞弊,可有证据?”
“你......你卷子前后笔迹不一!”
李富贵喘着粗气,折扇乱挥,“定是换人代考!”
“哦?”
陈渊挑眉,从袖中抽出半卷宣纸,“这是陈某昨日草稿,不知李公子可识得此字?”
他展开纸张,露出开头那几行歪斜的字迹,周围考生纷纷探头,有人低声道:“确实一样......这是苦肉计!”
李富贵忽然拔高声音,指向王大人,“他与这穷酸秀才勾结,故意先抑后扬!”
此话一出,全场寂静,王大人脸色瞬间惨白,下意识后退半步。
陈渊见状,心中冷笑。
他早料到李富贵会狗急跳墙,却没料到竟会扯出王大人——看来这对主仆,早已慌了阵脚。
他转身对着围观人群,朗声道:“既然诸位怀疑陈某才学,陈某便现场默写《永乐大典》‘农政’卷片段,如何?”
人群中响起抽气声。
《永乐大典》成书不过数十年,多数卷帙藏于内府,民间难得一见,更遑论默写。
李富贵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声,他清楚记得,父亲曾花三千两银子,才从宫里偷抄出半卷“乐律”篇。
陈渊从容取过笔墨,宣纸在风中展开。
前世他研究过《大典》残卷影印本,此刻闭目回忆,指尖却如有神助,开篇“农者,天下之本也”便力透纸背,继而详述历代屯田之法,竟连永乐帝批注的朱笔小字都分毫不差。
当最后一个字落下时,人群中爆发出惊呼。
陈渊抬头,看见街角站着个灰袍老者,腰间挂着块无字玉牌,正捻须微笑。
那老者目光与他相接,微微颔首,转身消失在人群中。
当晚,学政衙门失窃的消息传遍全城。
陈渊刚回到学舍,便被衙役破门而入,为首的捕快掀开他的考篮,竟从中抖出一卷泛黄的名单。
“好你个陈渊!”
捕快冷笑,“私藏考生贿赂名单,该当何罪?”
陈渊却不慌不忙,示意捕快凑近些。
待对方弯腰时,他突然捏紧考篮夹层,只听“噗”的一声,红色粉末扑面而来,捕快惨叫着后退,捂着眼睛满地打滚——正是他今早撒在夹层里的辣椒粉。
“诸位看清楚了。”
陈渊举起考篮,露出内侧焦黑的痕迹,“昨夜有人潜入陈某房间,
试图将伪证塞入篮中,却不慎碰翻烛台。
这名单......”他指尖划过纸面,“墨色新鲜,分明是今日所写,如何能作数?”
衙役们面面相觑。
李富贵的跟班躲在人群后,见势不妙正要溜走,却被陈渊叫住:“张公子,你袖中藏的是什么?”
那人浑身一抖,怀里掉出半块印泥,正是衙门专用的朱砂印。
月色爬上屋檐时,陈渊独自坐在窗前,望着墙上的舆图出神。
指尖轻轻抚过应天府的位置,他想起白天那位灰袍老者——那玉牌样式,竟与前世明史记载的东厂掌印官符极为相似。
“看来,这局棋......才刚刚开始。”
他喃喃自语,摸出藏在鞋底的纸条,上面是今夜从张公子身上搜出的密信,落款处“李”字潦草,却与王大人玉佩上的刻痕别无二致。
窗外,秋风卷起一片落叶,啪嗒一声贴在窗纸上,宛如一枚小小的书签,标记着这个夜晚的秘密。
陈渊吹灭油灯,黑暗中,墙上的舆图仿佛泛起微光,江河湖海的轮廓渐渐模糊,却又在他脑海中变得愈发清晰——那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版图,而他,正站在改变它的起点。
醉仙居的雕梁画栋在暮色中泛着暖黄,檐角铜铃随江风轻响,恍若摇碎了一江星辉。
陈渊站在台阶下,望着门楣上“醉仙居”三个鎏金大字,想起原主记忆中母亲临终前的碎语,指尖不由得摩挲腰间碎玉——此刻,这块寒酸的青玉竟比李富贵的羊脂玉佩更沉。
“哟,这不是新科解元吗?”
尖利的嗓音从二楼飘来。
陈渊抬头,看见李富贵斜倚在栏杆上,身边环着两个轻纱覆面的歌姬,手中晃着的酒杯里盛着琥珀色的葡萄酒,“今日诗会乃江南名士雅集,你这穿补丁的也敢来?”
二楼传来低低的嗤笑。
陈渊抬步上楼,听见身后有书生低语:“听说他在府试现场默写《永乐大典》,当真是神童转世?”
“神童?
我看是沽名钓誉,醉仙居的诗会可没那么好糊弄。”
雅阁内,檀香混着脂粉气扑面而来。
主位上坐着个紫髯老者,正是南京兵部尚书周大人,身侧站着的灰袍老者让陈渊瞳孔微缩——竟是那日在榜下颔首的神秘人。
李富贵见他目光,故意提高声音:“周大人,这便是我常
说的凤阳穷酸秀才,今日特来领教诸位大人的才学。”
“哦?”
周大人抚须淡笑,“听闻陈公子对《春秋》颇有见解,今日何不以‘雪’为题,作一首应景之词?”
堂中霎时寂静。
陈渊扫过席间:李富贵捏着酒盏冷笑,几个文人装模作样地拨弄琴弦,唯有灰袍老者垂眸饮茶,指节轻叩桌面,节奏竟与后世《致爱丽丝》的旋律暗合。
“既如此,陈某献丑了。”
陈渊负手而立,脑海中闪过前世在长城上见过的雪景,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掠过箭楼,天地间只剩一片苍茫。
他开口时,声音竟比记忆中的风雪更冷: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......”头三句出口,席间已有人搁下茶盏。
陈渊续道:“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。”
周大人的手指骤然收紧,杯中的葡萄酒泛起涟漪。
当“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落下时,整个雅阁鸦雀无声,唯有琴弦“铮”地绷断一根,惊起梁上尘埃。
“好一个‘还看今朝’!”
灰袍老者突然击节赞叹,抬眼时目光如刀,“陈公子此词,气吞山河,不知可曾读过《孙子兵法》?”
陈渊心中警铃大作。
这老者看似闲散,实则句句暗藏试探。
他拱手道:“兵法未曾深研,倒是对《天工开物》中火器篇略知一二。”
此话一出,周大人猛地转头,与老者交换眼色——世人皆知,兵部正着力改良火器,却屡屡受挫于图纸不全。
夜色渐深时,诗会散场。
陈渊谢绝了歌姬相送,独自沿着秦淮河畔行走。
灯笼在水面投下碎金,远处画舫传来靡靡之音,他却敏锐地注意到身后三道黑影,正借着廊柱阴影悄然靠近。
行至无人处,黑衣人骤然发难。
为首者挥刀劈来,刀锋划破空气的声响让陈渊想起前世实验室的液氮罐——冰冷,且致命。
他侧身避开,指尖触到腰间荷包里的镁粉包,那是今日从醉仙居后厨顺来的打火之物。
“你们是谁派来的?”
陈渊后退半步,背靠石墙,故意让声音染上颤音。
黑衣人不答,刀光再次袭来,却在离他咽喉三寸处顿住——陈渊突然扯开荷包,镁粉在月光下爆发出刺目强光,三名杀手同时捂住眼睛,闷哼倒地。
“火器之法,首
重燃爆。”
陈渊拾起地上的刀,用刀背敲了敲杀手的头盔,“《天工开物》云:‘硝性至阴,硫性至阳,阴阳相配,如夫妇之合。
’你们用的刀锈迹斑斑,也敢来行刺?”
杀手们面面相觑,其中一人突然开口:“你......你怎会知道我们用的是锈刀?”
话一出口,便知失言,慌忙闭嘴。
陈渊冷笑,瞥见为首者袖口绣着的双鱼纹样——正是李氏商行的暗纹。
就在此时,远处传来马蹄声。
陈渊转身欲走,却见一辆青帘马车疾驰而来,车窗缝隙里露出半张脸,涂着丹蔻的手指正对着他的方向。
他心中一动,突然想起醉仙居二楼所见的景象:周大人与李富贵碰杯时,两人袖口竟都露出双鱼刺绣的边角。
次日,应天府衙贴出海禁案牵连名单,陈渊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当捕快闯入学舍时,他正对着墙上的舆图沉思,指尖停在泉州港位置——那是郑和船队的始发地,也是海禁案的核心。
“陈渊,你私通南洋番商,该当何罪?”
捕快抖开文书,却见陈渊不慌不忙地取出一卷羊皮纸,上面用炭笔勾勒着精密的航海路线。
“诸位可知,《郑和航海图》中,古里国方位有误?”
他展开图纸,指着苏门答腊附近海域,“此处标注‘水浅多礁’,实则三年前已形成新航道。
若不信,可派水师实地勘测。”
捕快们面面相觑。
陈渊趁热打铁:“再者,海禁案名单上的‘陈渊’,籍贯写的是‘苏州府’,而陈某乃凤阳府人,分明是冒名顶替。”
他掏出县试准考证,上面“怀远县陈渊”的朱印清晰可辨。
暮色漫入学舍时,捕快们终于散去。
陈渊坐在窗前,望着手中的羊皮纸,想起昨夜杀手袖口的双鱼纹。
他忽然意识到,李富贵背后的势力远比想象中庞大——从科举舞弊到海禁走私,这张网早已织遍江南官场。
窗外,秦淮河上的画舫依旧喧嚣,歌声里却多了几分肃杀。
陈渊摸出藏在墙缝里的密信,那是从杀手身上搜出的纸条,上面只有短短一行字:“灭口,勿留痕迹。”
落款处画着双鱼纹样,与周大人腰间玉佩上的刻痕如出一辙。
“看来,该去会会这位兵部尚书了。”
他喃喃自语,将图纸卷好藏入袖中。
墙上的舆图在暮
色中若隐若现,长江如银链蜿蜒,而他,正站在这银链的折角处,即将扯开笼罩江南的黑网。
更深漏尽时,陈渊吹灭油灯,独自踏上通往兵部衙门的青石板路。
腰间碎玉随着步伐轻晃,恍若前世实验室里的震荡器,一下下叩击着历史的闸门。
这一夜,他知道,有些东西即将改变——如同秦淮河水,一旦决堤,便再无回头之路。
乡试第二场,贡院号舍里弥漫着浓重的艾草味。
陈渊握着毛笔的指尖微微发黏,案头的凉茶早已凉透,却无人敢去添水——昨日巳时三刻,左邻号舍的考生突然口吐白沫倒地,监考立刻锁了号栅,整座贡院如被扔进冰窟。
“咳......咳咳......”斜后方传来压抑的咳嗽。
陈渊转头,看见一个清瘦书生正用袖口捂着嘴,面色潮红如涂丹砂,脖颈间隐约有红疹蔓延。
他心中一凛,这症状与前世见过的猩红热极为相似,而号舍密不透风,正是传染病的温床。
“大人!
有人染病!”
他拍响号板。
巡场考官匆匆赶来,却在看见考生红疹时连连后退:“闭紧门窗,不许声张!”
陈渊皱眉,瞥见对方腰间挂着李氏商行的双鱼佩饰——又是李家的人。
申时初刻,已有七名考生昏迷。
陈渊扯下腰带,蘸着凉茶在宣纸上写下“隔离、通风、淡盐水漱口”九字,卷成纸团抛向主考棚。
片刻后,主考官阴沉着脸走来:“陈渊,你可知扰乱科场是何罪?”
“学生只知人命关天。”
陈渊直视对方,“若再拖延,恐成大疫,届时满场考生皆难幸免。”
他顿了顿,压低声音:“李大人想必也不想,让这贡院变成第二个应天府西巷吧?”
主考官瞳孔骤缩。
去年西巷爆发痘疫,死了三十余人,事后查出是李富贵强占民房囤货所致。
他拂袖而去,片刻后,号舍木窗次第打开,新鲜空气卷着雨丝涌入,陈渊听见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干呕声——那是考生们在按他的法子漱口。
<酉时三刻,陈渊被单独带入主考棚。
主考官李邦彦居中而坐,指间转着一枚翡翠扳指,正是李富贵昨日在醉仙居把玩之物。
“陈解元果然急公好义。”
李邦彦似笑非笑,“不过本官听说,你方才在号舍调配药汤,
用的是......青霉素?”
此言一出,棚内气氛骤冷。
陈渊心中警铃大作,面上却不动声色:“学生只是依《千金方》改良了忍冬藤煎剂,大人何出此言?”
他早知古代无“青霉素”之名,却故意在熬药时加入发酵的米浆——那是他从《天工开物》中查到的土法提取抗生素手段。
李邦彦敲了敲桌面,侍从端上一碗黑汤:“听闻此药奇效,本官特意备了一碗,还请陈解元先试药。”
碗中汤药泛着古怪的酸腐味,陈渊扫过碗沿细微的褐色沉淀,心中明了——这是加了巴豆的毒汤,若他拒绝,便坐实“妖言惑众”之罪。
他伸手接过,却在入口前突然呛咳,汤汁泼在桌案上,竟将木纹腐蚀出斑驳痕迹。
“大人这药......”他抹了把嘴角,“怕是比疫病更致命吧?”
李邦彦脸色剧变,拍案而起:“你敢污蔑本官!”
话音未落,棚外突然传来喧哗,几个考生被架了进来,其中一人扯着李邦彦的官服大喊:“他袖口有李氏商行的绣纹!
方才想往我们药里掺东西!”
陈渊定睛望去,只见那考生手中攥着半片衣袖,双鱼纹样刺目至极。
李邦彦踉跄后退,撞翻了身后的药罐,陈渊趁机扫过他腰间玉佩——果然刻着与杀手、周大人相同的双鱼纹。
夜雨渐急时,陈渊被允许提前离场。
他撑着破伞走过贡院角门,看见墙角蜷缩着个小吏,怀里抱着个油纸包瑟瑟发抖。
“陈......陈解元......”小吏哆哆嗦嗦递过纸包,“李大人说,让您忘了今晚的事......”油纸包打开,竟是五锭雪花银,底下压着张纸条,写着“明日子时,城西破庙”。
陈渊冷笑,将银子塞进小吏怀中:“劳烦回复李大人,陈某明日必到。”
转身时,他故意将半片衣袖留在墙角——那是从中毒考生身上撕下来的,袖口绣着的双鱼纹,此刻在雨中泛着诡异的光。
子时三刻,破庙屋檐下雨水如帘。
陈渊摸黑绕过正殿,听见偏殿传来压低的对话:“......只要他喝了那碗汤,就死无对证......周大人那边已打点好,明日便以‘妖术惑众’之名拿下......”他摸出怀中的火折子,突然照亮墙面——李
邦彦与灰衣吏员的身影正在墙根交头接耳,手中捧着的木箱敞着盖,露出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绢条,正是科举夹带。
“李大人好兴致。”
陈渊 目光扫过木箱,“这些夹带,与三年前顺天府舞弊案的款式倒很相似。”
李邦彦浑身一颤,手忙脚乱去盖木箱,却被陈渊一脚踩住箱盖。
借着火光,陈渊看见绢条上赫然写着《春秋》策论答案,墨迹新鲜,分明是近日所书。
“你......你想怎样?”
灰衣吏员掏出匕首,却在看见陈渊手中的火折子时有了惧色——破庙堆满干草,一旦起火,三人都难逃厄运。
“不想怎样。”
陈渊微笑,“不过是请李大人明日带陈某去一趟李氏货栈,听说那里的米袋......格外厚实。”
他话音未落,窗外突然传来炸雷,震得梁上尘土簌簌落下,仿佛上天也在为这夜的密谋轰鸣。
暴雨如注的后半夜,陈渊跟着李邦彦潜入城南货栈。
门轴发出吱呀声,他按住腰间的火折子,闻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墨香,心中愈发笃定。
当第三层米袋被搬开时,露出的二十口木箱里,满满当当全是科举夹带,最底层的账本翻开着,“李富贵周邦彦”的名字在烛光下格外刺目。
“三年六成进士名额......”陈渊指尖划过账本,“李大人可知道,太祖皇帝曾说‘科举乃立国之本’?
你们这样做,是要挖断大明的根基!”
李邦彦扑通跪地,额头磕在青石板上:“陈解元饶命!
都是李富贵那畜生逼的......”话未说完,门外突然传来马蹄声。
陈渊吹灭火折,拽着两人躲到立柱后,透过门缝,看见李富贵带着十几个家丁闯入,手中火把将雨幕照得通红。
“爹!
那穷酸秀才呢?”
李富贵咆哮着踢翻米袋,“今日若不除了他,咱们都得完蛋!”
陈渊感到身后的李邦彦浑身发抖,指甲几乎掐进他的手臂。
他按住老人颤抖的肩膀,目光落在货栈角落的排水口——那是今晚唯一的生路。
就在此时,又一道惊雷炸响。
陈渊趁机推开李邦彦,抓起账本冲向排水口,身后传来李富贵的怒吼:“抓住他!
别让账本流落出去!”
他钻进狭窄的水道,听见火把噼里啪啦的声响越来越远,怀中的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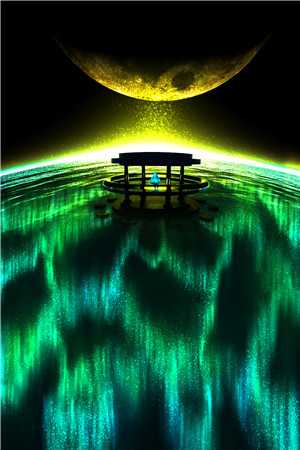
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