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女主角分别是林蓁苏芊芊的其他类型小说《结局+番外编号之外林蓁苏芊芊》,由网络作家“阿努比斯喵喵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1偌大的追思厅像一口被冰封的钟,时间被封存,空气稀薄,唯有冷光打在正中央那张巨幅遗像上——苏芊芊,黑白照里的她仿佛才刚从聚光灯下走下。林蓁站在厅角,黑色西装裙贴着身躯,掌心渗汗。没有哭声。连背景音乐都像被罩上了一层棉絮,沉闷而遥远。人群三三两两交谈着,仿佛这不是一场追思会,而是一场文学圈的集体亮相。苏芊芊——那位以《溃裂》一举成名的青年女作家,被称为“新时代女性困境写作的代言人”——一周前被发现在出租屋内自杀,遗书简短,死因迅速定性,火化时间仓促。林蓁觉得哪里不对。照片下是一行字:“感谢她留下光。”“她是光。”林蓁低声,像是在说给自己听。尤梨——苏芊芊生前的“长期合作者”——站在致辞台上,身姿挺拔,眼眶泛红,却语气稳重,像是早已练习...
《结局+番外编号之外林蓁苏芊芊》精彩片段
1偌大的追思厅像一口被冰封的钟,时间被封存,空气稀薄,唯有冷光打在正中央那张巨幅遗像上——苏芊芊,黑白照里的她仿佛才刚从聚光灯下走下。
林蓁站在厅角,黑色西装裙贴着身躯,掌心渗汗。
没有哭声。
连背景音乐都像被罩上了一层棉絮,沉闷而遥远。
人群三三两两交谈着,仿佛这不是一场追思会,而是一场文学圈的集体亮相。
苏芊芊——那位以《溃裂》一举成名的青年女作家,被称为“新时代女性困境写作的代言人”——一周前被发现在出租屋内自杀,遗书简短,死因迅速定性,火化时间仓促。
林蓁觉得哪里不对。
照片下是一行字:“感谢她留下光。”
“她是光。”
林蓁低声,像是在说给自己听。
尤梨——苏芊芊生前的“长期合作者”——站在致辞台上,身姿挺拔,眼眶泛红,却语气稳重,像是早已练习过千百次。
“芊芊曾说,她希望读者记住她笔下的坚韧,而不是她的离开。
她的创作未竟,我将替她完成。”
掌声寥寥,却整齐。
林蓁的视线越过人群,落在那封刚刚被主持人宣读完的“遗愿信”上。
——不是她的语气。
她读过太多芊芊的文字。
字句节奏、标点位置、常用比喻……这一封“遗愿”,没有一点属于她。
那句话还在耳边回响:“她希望你们记住的,是坚韧。”
可真正的坚韧,从来不是“跳海”,而是“转身回来”。
她记得《溃裂》出版前,芊芊还和她争论章节结构。
她说女主不能死。
但最终出版的版本里,女主在海边投海自尽。
此刻,有位年轻女读者踮脚挤到林蓁身边,小声问:“你是她大学同学吧?
请问小说最后那个结局,是她自己改的吗?”
林蓁怔住:“你说跳海那个?”
“对啊,她之前在直播里说不是这个结尾,可后来就突然改了。
是不是出版社让她改的?”
林蓁望向人群另一侧,尤梨正巧与一位出版社编辑握手,姿态得体自然。
像一切都尽在掌控。
她却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:她已经不是芊芊生活里的一部分了。
但如果她不发声,芊芊可能真的永远消失。
林蓁在心里悄悄写下四个字:这不对劲。
她不知道自己即将走入的,是一个用文字织成的巨大陷阱。
她只知道,她要开始重新读那部小说——从头到尾,逐字逐句,找到那个被人篡改的她。
2林蓁在第三天清晨回到芊芊的公寓。
那是一间租在文艺园区边缘的小屋,客厅不大,书桌靠窗,书架歪歪斜斜堆着未打包的书和杂志。
阳光穿透百叶窗,落在散乱的纸箱上,有一张手稿从中滑落,纸角泛黄。
门口残留着芊芊常用的雪松与柑橘味熏香。
气味很淡,却让林蓁瞬间心跳一滞。
“我只是来确认些事。”
她轻声说,好像怕惊扰谁。
书桌上摊着那台旧笔电。
她插上电源,屏幕慢慢亮起,背景是两年前她们一起去海边时拍的照片:芊芊站在岩石上,背光模糊,面容藏在霞光中。
桌面只有一个文件夹,名叫:“Final(真的最后)”。
她点开,弹出唯一的文档:Ch14-Draft4.docx。
林蓁眉头一跳,打开。
七页文字,最后修改时间显示为苏芊芊去世前三天。
——是她本人账号所留。
林蓁屏住呼吸,慢慢往下看。
“她站在岸边,不再往海里走了。
风从背后吹来,她听见一个声音说:回来吧。
于是她转身,迟疑而坚定地走回来。”
这一幕,彻底改变了整个结局的走向。
因为她记得,出版版本的《溃裂》,第十四章的结尾是:女主站在海边,自述“我不属于这个世界”,然后纵身跃下。
语言冷峻,结局沉寂。
可在这份文档中——她活了下来。
不是润色,不是删改,是意图与立场的完全反转。
林蓁迅速拍下文档属性,记录时间戳。
她犹豫片刻,拨出一个号码。
“我找到了《溃裂》的一个旧版本。”
她开门见山,“结尾和出版的完全不同。”
电话那头是尤梨,语气一如既往地温和,“你是说哪一份?”
“桌面上的Final文件夹,Draft4,三天前修改的版本。”
“哦,那应该是她之前备份的草稿。
你知道芊芊,她习惯写很多版本反复改。”
“但这个版本,她让角色活下来了。”
林蓁加重语气,“你确定出版时用的是她本人最终确认的稿?”
对方沉默了几秒。
“我们是根据她交给出版社的文档定稿的。
流程都有记录。”
“可我现在手上的是她本人留下的版本。”
林蓁
语气渐冷,“你们删掉了她的结尾。”
“你是不是太情绪化了?”
尤梨叹了口气,“你们关系近,我理解你的不舍,但这不是追责的方式。
你得有证据。”
林蓁望着电脑屏幕,唇角绷紧:“我会找到的。”
她挂断电话,转身坐回桌前。
阳光洒在那台旧笔电上,屏幕依然亮着,像是某种残留的见证。
她低声说了一句芊芊常挂在嘴边的话:“别急,我们从头来。”
这一次,她不会放过任何一行字。
3林蓁在图书馆打印那份合同复印件时,指尖发凉。
《溃裂》联合创作协议。
她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组,却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意那两字——“联合”。
第一页清晰标注:创作方甲:尤梨。
创作方乙:苏芊芊。
责任划分为:甲方负责整体架构与文本润色;乙方负责原始文本草案与推进节奏。
附件里有一行特别醒目的条款:“在乙方缺席的情况下,甲方有权决定最终文本安排。”
林蓁盯着“缺席”两个字。
她脑海里闪过一个词:死亡。
她拿出手机翻出几个月前芊芊转发给她的那份合同草稿截图。
上面标注的是:创作方甲:苏芊芊。
创作方乙:尤梨。
责任划分也截然不同:“乙方协助草稿整理,最终版本以甲方审定为准。”
她将两份合同打印出来,放在图书馆阅览桌上,一左一右。
纸张、字体、行距、签名笔迹——一切都很接近,唯有最关键的责任顺序被调换了。
林蓁用笔轻轻圈出那条授权句。
“你们谁改了时间线?”
她拨通尤梨的电话。
“我找到一份新版本的合同,上面写你是甲方。”
她冷静开口,“你能解释一下顺序是怎么变的吗?”
“那是我们补签的版本。”
尤梨答得毫不迟疑,“出版那会儿有些流程没走完,法务要求我们根据实际执行来重新梳理权责。”
“可你知道她从未授权你更改最终文本。”
“她口头同意过。”
林蓁冷笑,“她如果同意,为何留下的那一份是另一种结局?”
尤梨沉默。
“你到底想要的是她的作品,还是她的名字?”
林蓁咄咄逼问。
“林蓁。”
对方的语气忽然低了下去,“我们都失去了她,我只是在尽可能让她被记住。”
“可她不该被你改写。”
她挂断电话,靠着椅背坐下
。
那张合同纸像一把钝刀,慢慢剥开一个藏得很深的真相:有些被夺走的,不是名字。
是说“这是谁写的”这句话的权力。
4林蓁是在深夜整理芊芊旧物时,听到那段录音的。
那台早已停用的安卓手机,卡顿、发热,每次触摸屏幕都像在翻一页沉重的档案。
录音文件没有名字,只有一串混乱的数字。
她点开。
起初是一段静默——风声、远处汽车碾过水坑的哗响,还有偶尔一两声模糊的呼吸。
然后,是芊芊的声音,微哑而迟疑:“这不是我想写的。”
林蓁整个人坐直。
“她说市场不接受这样的结尾,说角色要有戏剧性。
但……我写的不是悲剧,我写的是幸存。”
短暂沉默后,又一段声音响起——那是尤梨。
“你太软弱了。
这个角色没说服力,观众不会买账。
你不觉得她死掉,更真实吗?”
“可我不想让她死。”
芊芊低声反驳,“她已经走到那一步了,她有资格活下去。”
林蓁听到这里,掌心出汗。
录音总长不过三分钟,却像剖开了整个作品的动机。
她记得芊芊曾在微信上和她说过:“我不想再写那些为了表达痛苦而死的角色。
我想写个撑下来的人。”
她以为那只是情绪吐槽。
可现在,这录音成了唯一的证据——芊芊是主动写出“生”的结局,却被他人劝改。
录音最后,芊芊的声音几不可闻:“他们不会听见的……他们只会看最后一版。”
林蓁缓缓闭上眼。
她打开笔记本,将录音一字一句地誊写出来。
那一夜,她抄写到凌晨三点。
指尖冰凉,眼眶泛红。
可她知道,她必须记住每一句话。
因为那是芊芊——最后的声音。
5林蓁约见褚怀义,是在一家永远光线昏暗的咖啡馆里。
对方比她预想中要瘦,头发稀疏,神情谨慎。
他是《溃裂》出版方的执行主编,也是整个合同流程的最终把关者。
林蓁摊开录音、合同打印件,以及那份最终文档。
“我只问一个问题。”
她开口时语气平静,“芊芊的稿费,到账了吗?”
褚怀义拿起文件翻了翻,手指微抖。
“我们是照流程走的。
按她和尤梨的分账比例——七三分,她三,尤梨七。”
林蓁盯着他,“可我从她的银行流水里查不到转账记录。”
“她……是
用第三方代收的账户。”
褚怀义目光游移。
<“可她从不委托别人收款。”
空气陷入短暂凝滞。
林蓁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打印好的收款记录截图,指着银行账号末尾,“这个账号,不是她的。
是尤梨的公司账户。”
褚怀义脸色终于变了。
“你是想说——我们侵吞了她的稿费?”
“我是说,她死前一个月,所有财务记录里,只有演讲费用入账,小说分成为零。”
“这是合约行为。”
他摆出职业口吻,“她签字了。”
林蓁冷笑,“如果我拿出她签署前的合约原件,而上面责任划分和账户信息完全不同,你是否愿意接受笔迹鉴定?”
褚怀义语气一顿,“你到底想怎么样?”
“我想要真相。”
“真相是什么?
是你觉得你朋友被人害死了,被人篡改了书?
可她早就精神状态不稳,她的合作者一直在照顾她——照顾她,还是控制她?”
褚怀义咬紧下唇。
林蓁起身,“你可能觉得,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文学争议。
但对我来说——这是她的遗言。”
她走出咖啡馆时,手机震动。
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讯:你越界了。
她早说过不想让你插手。
林蓁愣了几秒。
她没有告诉任何人,今天要去见褚怀义。
她抬头望向街对面,那是城市最常见的监控摄像头。
她忽然意识到,自己查的可能不是一本小说。
是一整套,建立在他人身份之上的利益系统。
6那是一段在文学杂志栏目中被广泛引用的访谈。
标题是《以她之名:写作双生对谈》。
林蓁坐在学校图书馆旧刊库的角落,翻着那本已经泛黄的杂志。
杂志上印着两位女性并肩而坐的照片——苏芊芊和尤梨。
那一年是她们刚因《溃裂》的试刊版本引起圈内注意的时候。
她们穿着素色衬衣,看起来更像一对双胞胎,而非创作搭档。
主持人问:“你们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?”
芊芊答得简短:“我写初稿,她帮我整理,给我反馈。”
尤梨却笑着补充:“她写得太快了,有时候稿子跟不上节奏。
我的工作更像是过滤器,帮她理清思路。”
林蓁盯着那段话。
这是最初的权力倾斜,隐藏在“协助”与“过滤”之间的微妙控制。
访谈中还提及一个细节:主持
人:“你们会在创作过程中争论吗?”
芊芊:“她会说我太理想主义。”
尤梨:“我只是更现实一些。”
现实。
在“现实”的名义下,芊芊一次次退让。
结尾变得模糊,人物开始消音。
林蓁翻到最后一页,那里有一段芊芊的自述:“有时候我会觉得文字不是我写出来的,而是她帮我翻译的。”
林蓁抚着那一行,指尖微颤。
那是一种失语的预告。
那晚她将整篇访谈逐字录入电脑。
次日,她向杂志社调取原始采访录音的申请被婉拒,理由是“资料遗失”。
可林蓁并不死心。
她顺藤摸瓜,找到当年做文字转写的实习编辑。
对方已离职,在家带娃。
视频电话那头的她眼神略带犹豫。
“我记得那期访谈……有一段没发出来。”
“哪一段?”
“芊芊说,她后来不太敢看自己写的文字。
她说,每次被尤梨改过以后,她就觉得那不再属于她。”
“你还留着那部分音频吗?”
女人迟疑片刻,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 U 盘。
“我只能帮到这儿了,你确定要查下去?”
林蓁点头。
她必须还芊芊一个真正属于她的声音。
7芊芊留下的备忘录不是日记。
它没有标题,没有时间顺序,也没有情绪记录。
更像是某种对抗遗忘的抗议。
林蓁在芊芊卧室的抽屉底部,找到那个老旧的笔记本。
封皮斑驳,上面贴着一张便利贴,写着:“别看——连我都快不记得了。”
她翻开第一页,是一句话:“如果哪一天我不再坚持那个结局,提醒我——那不是我。”
接下来的每一页,像是芊芊与自己对话的记录:“她说这样才有张力,可我写的是挣脱,不是沉没。”
“再改下去,这就不是我写的故事了。”
“她说观众爱看撕裂感,我说我想要缝合感。”
“如果我的名字被留在封面,那故事必须是我活过的样子。”
林蓁翻到最后几页,字迹开始变得凌乱。
“梦里我看见她披着我的稿子走进录音棚,她读得比我还顺。”
“我怕有一天,她会比我更像我。”
“她开始告诉我,这段也许你不该写,这个你可能太极端。”
“可这是我的疼,是我写的。”
“你知道什么是最可怕的吗?”
“当你说出的每一句话,都被她更换语序、润色语气后,变成
她要说的话。”
林蓁看着那句,怔了很久。
那是一种悄无声息的身份剥夺。
她将整本笔记拍照、编号、录入数据库,像整理一份犯罪现场记录。
最后一页,只有一句话:“写下去,不要被她删。”
林蓁合上本子。
她忽然明白——芊芊不是没留下痕迹。
她早就预感到这一切。
她用尽全力,在自己的名字被替代前,埋下了这些字句。
林蓁轻声道:“我收到了。”
8林蓁是在芊芊去世一个月后,联系到她的心理咨询师——关意晚。
她原以为对方会拒绝配合,毕竟病人隐私守则严苛。
可当她说明来意时,电话那头沉默片刻,随后轻声说了句:“我等你很久了。”
那是一家不起眼的心理咨询所,白墙,绿植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柚木香。
关意晚看起来三十出头,眼神清澈,说话不急不缓。
“我不能给你她的完整记录,但我可以告诉你,她在最后一次咨询时,说过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。”
林蓁屏息以待。
“她说,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了。
只要我写,她就会改。
只要我说,她就能更流畅地复述一遍,好像我原本就不会表达。”
关意晚轻叹,“她像是在描述一种……人格吸收。”
林蓁喃喃:“人格吸收?”
“她不是被剥夺表达权,而是逐步被训练成失去表达能力。”
林蓁怔住。
关意晚起身,从柜子里取出一张打印稿。
“这是她授权我保留的书写练习之一,她写得非常混乱,应该是在强烈情绪下完成的。”
林蓁接过。
那张纸上只有一句话,被重复书写了十余遍:“我想说的,不是她说的。”
有几行字被反复划掉,墨迹晕染成团,像一张极度压抑的情绪波动图。
“她曾试图断联。”
关意晚说,“三个月前,她来找我时说,她要结束这段合作关系。
她尝试提过几次,都失败了。
她说尤梨会哭,会劝,会说没有你我也活不下去。”
“情绪操控。”
林蓁低声。
“她说,最可怕的是她开始相信——她活不下去。”
林蓁望着那张纸,那些歪斜重复的字句,像某种呼救信号。
她曾拼命抗争过。
哪怕没人听见。
9林蓁在邮箱里找到那封转发邮件,是芊芊去世前一个月发出的。
标题是:
《新合同授权草案(暂存版)》。
正文只有一句话:“这份你帮我看一下,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”
附件名为《授权发布书 _final.docx》。
她点开那份文档。
页面干净整洁,语气客观。
但林蓁立刻看出问题:第一条条款写着——“甲方(苏芊芊)确认放弃对《溃裂》最终版本的审定权,全部文本由乙方(尤梨)代表整理发布。”
第二条:甲方自愿授权乙方以其名义参与出版、宣发与衍生开发。
第三条:甲方理解并同意,在不可抗因素或精神状态不稳定期间,乙方有权临时主导后续事务处理。
林蓁的指尖开始发冷。
她很清楚,这不是“联合创作”,这是“全面让渡”。
她立刻拨通一位法律系朋友的电话,对方看完后沉默许久。
“这份文书……如果真的签署了,那就是一份具备法律效力的自愿性身份代言授权书。”
“但她不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。”
“重点就在这。”
律师语气低沉,“如果她签署时心理状态已经存在异议,那么这份文书可以主张无效。”
“可你得证明她当时的精神状态。”
林蓁翻出心理咨询记录、录音整理稿、纸质笔迹对比图。
“我会证明的。”
她把合同打包寄给专业鉴定所,请求字迹比对。
那一晚她辗转难眠,脑中不断浮现芊芊坐在桌前、反复修改文档的样子。
她太熟悉那种眼神——疲惫、游移、不甘。
而那份授权书上,签字落款处的“苏芊芊”三个字,不带一丝起笔顿挫。
她敢断定。
那不是她签的。
10林蓁将部分证据发给了一位文化评论自媒体主编。
她没用实名,只附上一句注释:“一个作家死前失去了署名权。”
她本以为这消息会像火星落入干柴。
可两天过去,毫无动静。
第三天,她收到一封匿名回复:“内容极好,但无法转发。
对方律师函已经送到我们邮箱。”
她明白了。
这个行业的消声,并不需要谁动手。
只要没人愿意听,就足够了。
她尝试联系更多编辑、记者、独立撰稿人。
有人回得礼貌:“建议先核实相关授权关系。”
有人干脆拉黑。
有人只回一句:“你是当事人家属吗?”
她不是。
她只是见证者。
这正是她无法容忍的事—
—一个人的声音,需要靠亲属关系,才算有资格被相信。
她回头查阅《溃裂》的最新版本,在评论区发现一个 ID 反复留言:“她活下来了,可书里让她死了。
那不是她写的。”
那个 ID 叫:@海边望月。
她点击进主页,是一个阅读博主,最近一直在更新对《溃裂》不同版本的批注。
她私信过去: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
十分钟后,对方回了三个字:“我认识她。”
林蓁心头一跳。
“能聊聊吗?”
对方回复位置:江桥小镇旧书仓。
她第二天一早坐车过去。
旧书仓是一家开在镇子边缘的独立书屋,环境幽暗,书架高耸。
她走进去,看到一个穿灰蓝色衬衣的女孩正坐在角落,用红笔批注一本散页的小说。
“你是海边望月?”
女孩抬头,点头:“我叫沈折。”
林蓁在她对面坐下,看清她面前摊着的是《溃裂》的早期连载本。
“我读过她最初上传的每一段。
那些文字不是现在出版的节奏。”
沈折说。
她抬头:“你在调查吗?”
林蓁点头。
沈折递给她一本影印本:“这是我整理的连载删改记录对照。
官方版本删掉了至少四段关键描写。”
林蓁接过,翻开第一页,喉头发紧。
那些被删掉的段落,正是女主从濒死状态中挣扎出来的过程。
沈折轻声说:“他们不想她活下来。”
那一刻,林蓁忽然意识到:真正的“删改”,从来不只是文字。
是存在方式。
是表达权限。
是“你有没有资格留在这个故事里”。
11那段录音,是林蓁在整理沈折提供的资料 U 盘时发现的。
文件名只有两个字母:YQ。
点开,是断断续续的语音记录,背景有杯子碰撞声,还有风扇在转动的低鸣。
“你知道吗,我其实很羡慕你。”
那是尤梨的声音,年轻时的,语气带着点醉意。
“我看你写字的时候,像是你整个人都沉进去了,好像你根本不用想,就能说出那些别人想不明白的东西。”
苏芊芊没说话。
几秒后,她轻声回了一句:“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能力。”
尤梨笑了:“对你来说当然不算。
但对我来说,那是……我一辈子都得学的事。”
又一段沉默。
“你有没有想过,哪天你不写了,会发生什么?”
“我会找别的事情做
吧。”
芊芊说,“我不是非得靠这个证明自己。”
“可你已经在证明了。”
那一瞬,林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寒意。
那不是赞美。
那是某种贪婪的靠近。
录音跳转到了另一时段。
尤梨的语气变得更轻:“我发现,别人总说你文笔好,可是你发言从来结结巴巴。”
“所以我帮你说啊。
你也不擅长应酬,我就去和编辑谈。
你不想录音,我替你读。
你不是说只想写字吗?”
芊芊没回答。
“你信任我,对吧?”
“……嗯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
林蓁听完这段音频,久久未动。
她意识到,那场“合作”的起点,并非压迫,而是亲近。
是一次倾慕、一次投射。
是“我不如你”衍生出的“我要成为你”。
尤梨不是一开始就夺走芊芊的声音。
她是一步步,从“帮你说”变成“代你说”。
从“共鸣”走向“同化”。
从“我喜欢你写的”,变成“我来写像你那样的”。
林蓁缓缓合上播放器。
她知道,该面对真正的对话了。
她拨通那个早已存在却始终未点开的号码。
电话那头响了三声,接通。
是尤梨的声音,低而平稳:“你终于想通了。”
12“你终于想通了。”
电话那头的尤梨,声音温和而笃定,像一位早已等在终点的讲述者。
林蓁没有回应。
“你是不是在看那些旧文档?
芊芊的录音?
还有那份合同?”
“我看到的,是你逐步占据她生活的证据。”
林蓁声音冷硬,“你从代写到代发,从代理人到署名人。”
尤梨轻笑:“你以为我想要那些吗?”
“你不是吗?”
“我只是想帮她留住被世界遗忘的部分。”
林蓁沉默几秒,“可你抹掉的是她自己。”
电话那头响起椅子被轻轻拖动的声音,仿佛尤梨坐了下来,准备好讲一个早就编织好的故事。
“你知道她有多胆怯吗?
她怕镜头,怕采访,怕签售会那种热度。
她说她只想写东西,可她写的东西,一旦被看到,就要承担回应。”
“那是创作者的责任。”
“可她不想承担。”
尤梨打断她,“她说她想当个影子,作品自己走路,她不想出现。”
“可你却走出来了。”
“是她让我走出来的。”
林蓁呼吸一滞:“你在说什么?”
“她说,如果你比我更能保护这些故事,那就交给你吧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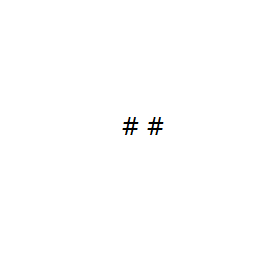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